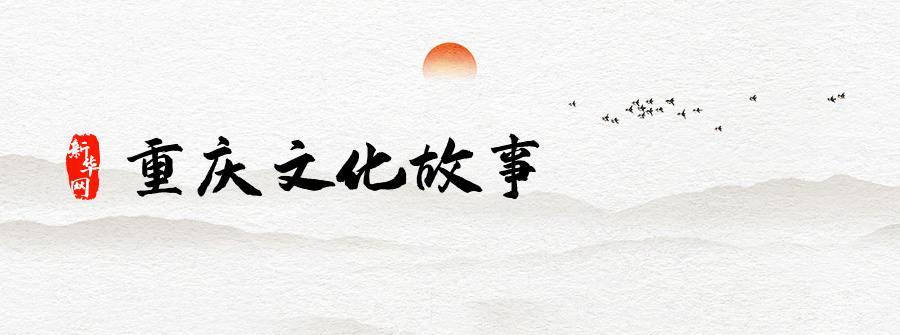
文/夏显虎 曾启华
没有人想到,深层泥土中埋藏着6000年前的惊人场景。
1992年,实施三峡库区文物保护规划时,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调查中发现了丰都玉溪遗址,并于1994年4月进行了试掘。自1998年以来,重庆市博物馆和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对玉溪遗址进行了6次大规模发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商周、唐、宋、明、清等多个时期的遗存,其中新石器时代、唐宋时期的遗存是玉溪遗址的主体遗存,堆积尤其深厚。
惊人的秘密就在向下深挖中赫然显现。
玉溪遗址在重庆市丰都县高家镇金刚村,遗址北面紧邻玉溪河,西临长江,属临江阶地型遗址。玉溪遗址顶部海拔约155米,三峡大坝蓄水前,玉溪遗址顶部高出常年平水位约28.5米,高出常年洪水位约10米,正是古人类逐水而居的理想阶地:土壤肥沃,生产生活方便。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这理想的聚落阶地上,曾经发生一次又一次悲剧。
玉溪遗址发掘厚度约7米,共划分31层,其中,上部1至9层以文化层为主,夹杂少量碎陶片和石器碎片,下部10至30层则以薄层骨渣层为主,夹杂各种动物碎骨,这些都是玉溪古人类生息于此的遗存物,悲剧的印记就断续出现在这些遗存物的间隔区域。
揭开遗址表层的耕土层,逐次向下是明清至现代文化层、唐宋时期淤积层,第三层是约距今5500至4800年前的玉溪坪文化层,第4至8层是距今6200至5800年前的玉溪上层文化早期,第9层为距今6300年前的玉溪下层文化晚期。发掘继续向下进行,揭开第10层,是一层厚厚的纯净淤积砂土,没有人类遗存物。继续向下发掘,从第11层至21层间,竟有至少5层厚厚的纯净淤砂层,同样没有人类遗存物。这11个地层对应距今6467年至6407年前共60年的历史,即在这短短的60年间,长江上游地区至少发生了5次特大洪水事件。
研究发现,这几次特大洪水的规模都在海拔158米高程以上,即这几次特大洪水至少高于玉溪遗址顶部3米,摧毁了包括玉溪遗址在内的长江沿线诸多古人类聚落。

图为丰都玉溪遗址全景。丰都县文管所供图
由于科学结论需要排他性证据,玉溪遗址发现的特大古洪水遗存被考古工作者谨慎地称作“疑似古洪水”。这些疑似古洪水淤砂层平均厚度28厘米,最厚81厘米,最薄10厘米,表明各次特大洪水的规模有较大差异。在没有科学气象手段的远古时期,无规律的洪水使古人类失去了经验预防的能力,必然造成灾难性后果。
发掘过程中,为了还原更为精确的远古生活场景,考古工作者将玉溪遗址地层分为74个小地层,其中,第1层为现代耕土层,2层为明清至近代层,3层为唐宋时期的堆积,4层为新石器末期,5至9层为新石器晚期,10至14层为新石器间歇层,15至74层为新石器中期。
历史从远处走来,最深地层距今时间最久远,因此我们要从下至上分析,才能弄清距今6000多年前玉溪遗址自远而近的变迁场景。
发掘发现,玉溪遗址考古地层第67层为疏松纯净的青色砂土,没有发现人类遗物,第65层为细密的黄灰色砂土,且含有大量石粒,第64层为疏松而纯净的灰黄色砂土,第60层为极细密、极纯净的灰黄色砂土,说明这一时期的特大洪水反复发生,家园被摧毁,玉溪古人类撤出了这一聚落地。
第58至50层发掘出多寡不等的人类活动遗存物,说明玉溪古人类在大洪水完全退却后,回到这里重建他们的聚落生活,并较长时间处于安定状态。但是,第48至46层为紧密的黄沙层,人类活动痕迹消失,说明大洪水再次摧毁玉溪古人类的生活。专家认为,玉溪遗址下层频繁快速堆积的淤砂层是气候剧烈波动、水文异常变化的结果。通俗地说,这一时期气候极不稳定,导致大洪水反复发作。
玉溪遗址第43至26层仅发掘出极少量人类活动遗物,这一时期玉溪古人类又回来了,但是他们的生活规模变得很小,零零星星,原因何在,尚无结论。
第22层含少量骨渣、石片、螺壳,第20层含零星石片、动物残骨,第18层含零星炭粒和螺壳,它们都是玉溪古人类活动的遗存物。这一时期仍是大洪水间隙,玉溪古人类的生活仍在战战兢兢地继续。
第16层发掘出少量石制品、动物残骨和灰烬,聚落生活仍在小规模继续。第14层为浅青色紧密砂土,含较多石粒,没有人类活动遗存物,第13层是紧密的浅青黄色纯净砂土,同样没有人类活动的遗物,第12层为纯净紧密的深黄色砂土,没有任何文化遗物。这一时期的洪水抹去了玉溪古人类活动的所有痕迹。

图为丰都玉溪遗址全景。丰都县文管所供图
研究发现,玉溪遗址古洪水高于海拔147米的,大约每48.1至42.2年发生一次,这一高度比远古常年洪水位高出近10米,沿江古人类往往根据常年洪水经验,而选择在这关键的10米范围内从事日常生产生活,距今6400多年前的60年内就发生了5次特大洪水。
发掘发现,从玉溪上层文化阶段(约距今6000年前)开始,玉溪遗址的洪水遗迹突然大大减少,有可能是气候迅速从湿热多雨转变为高温少雨所致。考古发现,玉溪古人类在这一时期突然从渔猎采集经济转变为台地旱作农业,这一现象也证明气候发生了巨大变化。大洪水周期变长,雨水变少,新的烦恼困扰着玉溪古人类的生产生活。
地质学家杨怀仁先生认为,距今8000至6000年前是华北平原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第一洪水期,期间,南京地区至少经历了4次较大规模的洪水——杨怀仁的断论正与玉溪遗址古洪水遗存信息相互佐证。
研究发现,距今7200至6000年前是全新世大暖期的鼎盛期。玉溪遗址在短短60年内就遭遇5次特大古洪水,正是湿热多雨的气候所致。从距今6000年前开始,全新世大暖期鼎盛期基本结束,进入气候剧烈波动的冷干期,干旱少雨,这一研究结论也与玉溪古人类突然从渔猎经济转变为旱地农业的现象互相印证。
统计发现,从东周到清代的2500年内,长江流域可考的水灾为255次,平均周期为9.73年一次。
虽然自古以来大洪水对长江沿线破坏巨大,有关三峡地区先秦时期的洪水记述却相当稀少,且是笼统的传说或神话,从科学角度记述距今4000年以前长江三峡地区洪水史实的,一条也没有(杨华《三峡考古文化》P.526)。《中国气象灾害大典·重庆卷》记载的暴雨洪涝灾害,有关先秦时期的仅有一条:“夏禹时代,云阳,长江洪水暴涨,县城受损严重。”第二条就是西汉时期了。重庆三峡地区先秦时期唯一的这一条洪涝记载,尚语焉不详,或源自民间传说。然以淤砂层为严格依据的环境考古却还原出一个又一个史前大洪水的真实景象,使原本不可信的传说落地为史实。丰都玉溪遗址第11至21层揭示的,乃距今7000至6000年前长江中上游地区特大洪水的发生景象,远在夏禹治水之前2000余年,弥足珍贵。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自白九江、邹后曦、朱诚《玉溪遗址古洪水遗存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科学通报2008年第53卷;徐伟峰、朱诚《长江三峡库区玉溪遗址地层沉积特征研究》,地层学杂志2008年1月,第32卷第1期;史威、朱诚等《重庆丰都玉溪剖面的沉积学和气候意义》,沉积学报2010年2月,第28卷第1期)



